读《呼兰河传》有感
时间: 07-18 来源:乐乐
曾有人说过,想起张爱玲,那是一个泛着华美微光的苍凉手势。而读萧红的文字,则感受一种回荡在荒野上的寂寞低吟。 萧红的呼兰河是她童年的家园。“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,则大地满地裂着口。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几尺长的,一丈长的,还有好几丈长的,它们毫无方向地,便随时随地,只要严冬一到,大地就裂开口了。”这样一个东北小城,风土人情,来往婚嫁,平常起居,萧红淡淡的叙述,精心地刻画。她写卖馒头的老头、东二道街上的扎彩铺、一个提篮子卖烧饼的,又一个卖凉粉的,“卖凉粉的一过去了,一天也就快黑了。打着拨浪鼓的货郎,一到太阳偏西,就再不进到小巷子里来,就连僻静的街他也不去了,他担着担子从大街口走回家去。卖瓦盆的,也早都收市了。拣绳头的,换破烂的也都回家去了。只有卖豆腐的则又出来了。” 偌大的一个城,来来往往的人,能干的就那么几件事,能过得就那么一种生活。这儿的人最热衷于干的事就是看热闹,甚至只是一个女人追赶孩子的闹剧,就可以让周围的人看的兴趣盎然,全然忘记了自己。甚至由此还会发出今天过得真有趣的感慨。
没有一个外来的人打破这死寂的生活。这样的小城,一点点把你拉进时间静止的暗域,挣扎不得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 茅盾说:“读萧红的作品,开始有轻松之感,然而越读下去,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。”
萧红以犀利的笔锋剖析了人们灵魂中哪种可怕的惰性。比如那个泥坑子,“老头走在泥坑子沿上,两条腿打颤,小孩子在泥坑子的沿上吓得狼哭鬼叫。”然而“一年之中抬车抬马,在泥坑子上,不知抬了多少次,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?没有一个!”呼兰河的历史,小人物的悲欢,都在冷静的笔调下娓娓道来。既有画卷般的乡土风情,也有压抑的蒙昧人性。她爱这座小城,却决不苟同。一直逃离命运的把握,却又一直想回到那个温暖的掌心。矛盾、冲突、现实与童心,交织着呼兰河城的气息,像有些发霉的棉絮暴露在阳光下,气味阴湿,但你绝无法抛弃它的旧日温暖。
呼兰河的寂寞,萧红明白,萧红的寂寞,又有谁明白? 萧红父亲残暴,母亲早逝,幼年生活里仅存的温暖是祖父的疼爱。后来她受逼婚离家,只身到北平。再后来为逃避敌人追捕,流亡关内,及至晚年因肺结核死亡,年仅31岁。
在萧红的作品中,她从不回避残酷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幸,她描写贫困、饥饿、疾病、灾难,展现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人生。但在《呼兰河传》里,她依然倾注了爱意与童心,不乏诗意与抒情的笔调。那是因为有祖父,有他的后花园。书中也写过:“祖父不怎样会理财,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。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;我想,幸好我长大了,我三岁了,不然祖父该多寂寞。”
这样的一个花园,“这花园里蜂子、蝴蝶、蜻蜓、蚂蚱,样样都有。蝴蝶有白蝴蝶、黄蝴蝶。这种蝴蝶极小,不太好看。……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,红的红,绿的绿,新鲜漂亮。”“说也奇怪,我家里的东西都是成对的,成双的。没有单个的。砖头晒太阳,就有泥土来陪着。有破坛子,就有破大缸。有猪槽子就有铁犁头。像是它们都配了对,结了婚。” 小主人公,和她和蔼的祖父,使得这死灰般的生活底布上显现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与祖父在一起的日子让人看得兴致勃勃,无端地艳羡,“玩腻了,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,祖父浇菜,我也抢过来浇,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,而是拿着水瓢,拼尽了力气,把水往天空里一扬,大喊着:‘下雨了,下雨了。’”
看到这儿,不由得会心一笑,可亲可爱的祖父,童真童趣的“我”,即使有“父亲的冷淡,母亲的恶言恶色,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,都觉得算不了什么。”他们过着桃源般的生活,无忧无虑。 这儿,是存在萧红心中的唯一想念,恐慌境遇中的祥和之地。就是在梦中,看到漫天无际飞舞的蝴蝶、蜻蜓,也会同样开心地笑出来,好像回到了童年的花园。
她一遍遍地重复,絮絮地讲述曾经的岁月,生活过的地方,放花灯的、唱台戏的、跳大神的,人们凑热闹,谈天说地,睡觉,吃饭,探亲……一切的细节,都是对祖父一起生活的深刻想念,对故园的渴求。 但,逃也逃不开的,是漂泊、游离、终苦一生的命运。
“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,而今不见了。老主人死了,小主人逃荒去了。 那园里的蝴蝶,蚂蚱,蜻蜓,也许还是年年仍旧,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。
小黄瓜,大倭瓜,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,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。” 萧红的文字,一以贯之地清淡平静、一以贯之地荒凉寂寞。她将命运的起伏不定都向内敛化,让世事的荒凉和悲壮都隐忍在文字后,如同种子般,深埋地下而包含巨大力量,开出一朵寂寞之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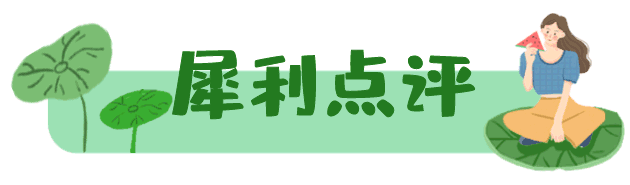
详略不当